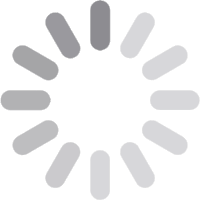[客座博主吉姆·奧爾布賴特]
凱茜、我們的兒子肯尼斯和我住在丹佛地區,當時我在聯邦監獄局參加考試、面試和體檢。我試圖在科羅拉多州恩格爾伍德的機構工作,但他們正在為明尼蘇達州監獄培訓官員,該監獄即將重新開放,所以他們當時沒有招聘。
在我等待他們再次開始招聘的同時,我繼續在 Sealtest Dairy 擔任卡車裝載機。一天晚上,我下班回家,凱茜說:“你今天收到了政府的一封信。這是惡魔島的典獄長P.J.馬迪根(P.J. Madigan)發來的,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在三藩市的約會。在我們把腫塊從喉嚨里弄出來后,我們商量了一下,決定接受這個提議,去那裡服我的第一個試用年,然後轉回恩格爾伍德。
我們賣掉了房子和傢俱,把所有剩下的財產裝進了一輛 1956 年的雪佛蘭 Nomad,然後前往加利福尼亞,以前從未去過比丹佛更西的地方。
當我們穿過奧克蘭海灣大橋時,我們可以看到海灣中的惡魔島。在那一天,島上籠罩著濃霧。對於我們幾個年輕人來說,這個景象非常不祥。我當時只有24歲,以前沒有執法經驗。我看了看島上,然後凱茜和我們19個月大的兒子肯尼在汽車後座上睡著了,我說:“我在#%@中做了什么?
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寓出租。這很艱難,因為人們會接受動物,但不會接受孩子。我們正準備給甘迺戴上狗項圈去找公寓,而且我們希望它靠近碼頭,我不得不登船上班。我們在80.00年發現了一個每月超過1959美元的人。我們在那裡住了大約三個月,然後在島上買了一套公寓。
在我們搬到島上后,這讓凱茜和甘迺登上了惡魔島的舞臺。他們忙於學習島上生活的規章制度,也結交了很多新朋友。
與此同時,我正忙於了解監獄工作的來龍去脈。我觀察了其他軍官,發現其中有兩三個我認為是好軍官。我和他們交了朋友,並以他們為榜樣。它一定奏效了,因為我在惡魔島工作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獲得了兩次晉陞。
我和家人安頓下來,學會了愛上這個島。我們有兩個女兒,Vicki,出生於1961年,Donna出生於1963年。事實上,唐娜是監獄仍在運作時出生的最後一個孩子。監獄關閉的那天,她才十一天大。從1963年3月21日到1963年6月22日,我被留在島上。這種延遲使我成為「最後的守衛」。。
當我們把最後27名囚犯帶離島上時,「雙重強硬」莫裡斯·奧德韋中尉讓我走到最後一名囚犯旁邊,護送他出去,所以我護送最後一名囚犯出去。
在惡魔島工作后,我留在監獄工作,結束了我的職業生涯,在五個不同的監獄工作了26年。我在印第安那州的特雷霍特退休,因為我最後在那所監獄工作,我們在那裡有一個家。
幾年後,我們聽說了島上一年一度的惡魔島校友會聚會,我是該協會的董事會成員。
我們參加聚會已經有大約20年了。可悲的是,惡魔島的工作人員或囚犯已經不多了。在我們最後一次聚會時,我們只有兩名警衛和一名囚犯參加。我們還剩下幾個人,但由於健康問題或距離,或兩者兼而有之,他們無法參加。
凱茜和我在2015年有過一次特別的重逢。我們得到了國家公園管理局的許可,可以更新我們的 60 周年結婚紀念誓言。約翰·坎特威爾(John Cantwell)是一名護林員,也是一名牧師,他在“A Block”中對惡魔島進行了服務。我們有22個親戚,大約50個惡魔島校友,還有很多很多非常親愛的朋友參加。 然後,我們有一艘惡魔島游輪船在島上接我們,在海灣周圍享用晚餐。

多麼美妙的回憶。
吉姆和凱茜·奧爾布賴特

 Discover Experiences Near Me
Discover Experiences Near Me